理论成果 
法律适用,不能带有情绪! ----对原徐州市市长陈耀南跑官案定性之质疑
刊登于《律师与法制》2003年第12期
法律适用,不能带有情绪!
----对原徐州市市长陈耀南跑官案定性之质疑
杭 正 亚
日前,一个离奇的案件正在被国内外各大媒体“炒热”。几个无业游民和打工仔略施雕虫小技,竟能以镇江市“书记”、“市长”的官帽为诱饵,骗到了时任镇江市委副书记陈耀南的头上,几个自告奋勇的跑官者为陈能“就地转正”而被骗百万巨款。这一案件算是一个丑闻,造成了极坏的政治影响。为挽回政治影响,证明党的纯洁性,就要对所有“买官”、“卖官”者从严惩处。法院对此事件作出三份判决,几个骗子犯诈骗罪,几个跑官者犯行贿罪,陈耀南犯受贿罪。
当社会公众为这一闹剧叫绝,为法院判决叫好之时,著名刑法学家对陈耀南跑官行为定性为受贿提出了质疑。2003年8月30日,中国法学会研究部邀请刑法学专家高铭暄、赵秉志、陈兴良、陈泽宪、方向对陈耀南案件中“买官被骗”一事进行了专题论证。专家们经过认真研讨分析,一致认为:“陈耀南案件中‘买官被骗’一事的性质,不应认定为陈耀南受贿,而属于李贤志、刘以江、蔡连银、陈耀南等人共同行贿未遂。
也许人们对案情的关注是出于好奇,而对法律适用的冷淡则由于法律条文的枯燥,除了刑法学家的论证以外,似乎人们对本案的法律适用问题已经熟视无睹,而变得冷淡。也许人们对案情的关注是出于好奇,而对法律适用的冷淡则由于法律条文的枯燥。笔者要不是在该案的二审后期参与了辩护工作及现在又担任申诉的律师,也许只能和大多数人一样,为这一闹剧而感到可恨、可悲、可笑!然而,作为一个争议极大的问题,笔者很难采取冷淡的态度。希望本文的观点不会使那些正气凛然的好人误解,认为我是以媒体为“辩护台”,替“坏人”说话。
对于本案的某些具体事实,一、二审法院的大致叙述清楚。一审判决认定:
镇江市委副秘书长李贤志为感谢陈耀南对其在职位变动、升迁方面的关心帮助并为今后继续得到关照,于2000年 5、 6月份与镇江新宏基房地产公司总经理刘以江商谈,欲为陈耀南的职务升迁找关系。后刘以江在北京结识了辽宁盘锦人“陈思宇”(真名侯万清),……陈思宇谎称可以帮忙,并要求约见陈耀南。……2000年11月 5日,李贤志、陈耀南到北京国际饭店,在与陈思宇、刘以江商谈中,提出想在镇江就地“扶正”(指提任书记)。当晚,陈思宇安排同伙孙德文假冒中央某领导人办公室副主任“陈刚”与陈耀南等人在饭店见面,席间陈思宇、陈刚询问了陈耀南的简历和工作情况,陈耀南表示愿意继续留在镇江工作,陈思宇、陈刚谎称就陈耀南“扶正”之事可以帮忙,并要求被告人陈耀南准备有关政绩材料速送北京。被告人陈耀南遂打电话安排镇江市委办公室副主任蔡连银准备了《几年来的回顾》等材料,后由李贤志将陈耀南所谓政绩材料交给陈思宇,陈思宇向刘以江、李贤志提出需要“就地扶正”费用 150万元。李贤志即返回镇江,将为陈耀南提拔筹资之事告知蔡连银,蔡认为这是好机会,就积极响应,二人就筹钱之事进行了商定,后李贤志又向被告人陈耀南汇报此事,并称筹钱之事由其与蔡连银负责,被告人陈耀南表示同意。
当月20日,李、蔡携带筹集的先期活动费用20万元、人民币 4万美金到北京。次日,被告人陈耀南亦到北京,蔡连银将人民币和美元存单交与其过目,被告人陈耀南当即指示:事情办不成不能给钱。后由刘以江常住北京联系催办,李贤志、蔡连银在镇江、丹阳等地从丹阳天工集团等处筹集款项,并多次往返北京、镇江二地打探消息。此后,陈思宇不断谎称“扶正”一事正在顺利进行,并以给有关人员送礼为名不断索要活动经费,至2000年12月中旬,陈思宇骗称事情已经办成,要求兑现全部费用,先后从李贤志、蔡连银处计骗得人民币132万元和美金 4万元。
2000年12月底,被告人陈耀南得知其将要调徐州市任市委副书记、政府市长后,自感受骗,多次召集李、蔡二人询问情况,蔡连银明确告知已为“扶正”一事花费 132万元人民币、 4万美金,并称由其与李贤志负责追回、偿还。后李、蔡二人追钱未果,由李、蔡二人与丹阳天工集团分别订立了债务分担及还款协议。
对于此起事实,被告人及其辩护人均提出被告人陈耀南的行为不构成受贿罪的意见,经查认为,被告人陈耀南明知李贤志等人为其“扶正”而花费应由陈耀南本人出的钱,其非但没有制止,反而表示“事未办成不能给钱”,其主观上具有收受李贤志等人贿赂和同意李贤志等人为其花钱“扶正”的故意,且从被告人供述看,其故意的形式是一种概括故意,只要是为其“扶正”花费,都不超出其故意的范围。其受贿虽未实际得到钱款,但此款用于其“扶正”,只是赃款的去向和用途,不影响受贿罪的成立。
二审裁定认为:
陈耀南虽然对“陈思宇”等人为此事索要钱款及李贤志等人实际支付钱款的具体数额不知晓,也未直接收受该款项,但其对李贤志等人为其“扶正”一事找人通关系、要为其筹集花费所款项之事是明知并认可的,主观上具有收受李贤志等人贿赂的故意,客观上李贤志等人筹集的人民币 132万元,美元 4万元已全部用于被告人“扶正”的活动之中,因此被告人陈耀南变相收受贿赂行为符合受贿罪的构成要件。
对于法院判决,笔者感到引起争议或质疑之处很多,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客观行为:是变相收受财物并为他人谋利益,还是跑官买官?
法院认定陈耀南变相收受李贤志、蔡连银贿赂132万人民币、4万美元,其理由是陈同意李、蔡二人“为其提拔、重用而花费钱财”人民币 132万元、美金 4万元。这一认定与事实不符:
1、从付款的数额看,陈耀南并不清楚陈思宇索要 150万元一事。在此问题上,二审裁定已经澄清。可以这样说,陈在知道李贤志等人为他“扶正”而活动并在事成后要花钱时没有制止,自己去北京的目的是想与所谓的“领导”见面,与“买官”花钱无关,相反却是制止李、蔡已经带去的20万元人民币和 4万美金为他“扶正”而花费。正是由于陈的反对,这笔钱当时又带回了镇江。
2、从付款的条件看,陈耀南不能对他人违背陈意见擅自付款的行为承担刑事责任。对于该款项,有先后的十次付款行为,而所有这些付款行为,在付款前没有陈的指示,在付款时没有陈委托,在付款后没有陈的认可,可以说交钱的事前、事中、事后根本没有向陈请示汇报。更为重要的是案卷中没有一份证据可以证明李、蔡、刘是认为“事情已经办成”的情况下给钱的,相反许多证据却证明陈思宇是在“事未办成”的情况下,以办事需要先后多次骗钱的。在事情没有办成的情况下付款是陈所反对的,李、蔡、刘等人违背陈“事情办不成不能给钱”的明确意见,致使巨款被骗。这一责任怎能由陈来负?
3、从付款的原因看,陈思宇是以陈耀南“扶正”和转让镇江国际饭店两个名义骗钱的。究竟用于陈“扶正”的费用是多少,当事人的供述之间都不一致,在判决之先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江苏省镇江市中级法院(2002)镇刑二初字第 5号刑事判决,认定“被告人侯万清先后 9次从刘以江处骗取费用共计人民币 106万元”,而法院无视已经生效判决所认定的事实,以“就高不就低”为原则,将所有费用全部算在陈耀南头上是相当不公正的。
4、从付款的主体看,是刘以江而不是李贤志、蔡连银。判决为了认定陈收受李、蔡二人的贿赂,无视所有款项是从刘以江处骗走的事实,错误认定:陈思宇“先后从李贤志、蔡连银处计骗得人民币 132万元和美金 4万元”。令人费解的是,为认定李贤志、蔡连银、刘以江向陈行贿,与该判决同一天、同一法院、除审判长一人不同外的几乎同一套审判班子、对同一事实作出的判决,却是这样认定的:“先后从李贤志、蔡连银、刘以江处计骗得人民币 132万元、美金 4万元”。可见,一审法院为判决而编写事实的痕迹是如此之重!实际上,钱是在刘以江手上被骗走的,镇江市中级法院(2002)镇刑二初字第 5号刑事判决关于“被告人侯万清先后 9次从刘以江处骗取费用”的认定是正确的。事后,刘以江还书写了借蔡连根人民币 168万元、美金 4万元的借条。人们不禁要问,如果李、蔡二人不肯分担债务,那么又是谁行贿?蔡对刘以江还有人民币 168万元、美金 4万元的债权,又说明蔡在承担债务的同时又有债权,财物并没有减少,凭什么说李、蔡二人向陈变相行贿?
客观行为的另一个焦点是,陈耀南有没有利用职务便利为李贤志、蔡连银谋取利益?判决中没有陈耀南为蔡连根谋取利益认定,但是却认定陈为李贤志谋取利益,这是不能成立的。因为,陈、李二人的表述不一致,一审判决是这样先后引用陈耀南、李贤志的供述的:“李贤志为我扶正的事这么热心的原因一是他认为我这个人还是不错的,二是他和我关系好,他希望我以后多关心他,另外,他从市政府副秘书长调到市委副秘书长是我提议的,他从丹徒镇党委书记到润州区任副区长也是我提议的。”“我给陈耀南办扶正的事原因一是对陈耀南感恩戴德,因为陈耀南对我的成长很关心;二是想找个靠山;三是想换个有权有钱的位置。”对这样表述不一的供述,怎能作为谋取利益的证据?即使是事实,所谓的利益也很笼统并不具体,更没有明确提出,都是各人单方面的猜测或想法,陈所说的一个“希望”、李所说的两个“想”,都是仍处于内心世界中的抽象,没有任何明确的意思表示。至于李贤志多年以前的工作调动,是陈提议的李不一定知道,也不会以这次为陈效劳来报答。因此,在“扶正”的事情中,陈、李二人之间并没有什么交易,更谈不上为他谋取任何利益。
另外,判决对谋取利益的认定与该院其它判决相矛盾。该院在对李贤志、蔡连银、刘以江的判决中,为证实蔡连银构成行贿罪,又这样认定:“三被告人是共同为陈耀南谋取的不正当利益,构成共同犯罪”。这又说明,不是“受贿人”陈为“行贿人”李、蔡谋取利益,而是相反即“行贿人”李、蔡为“受贿人”陈谋取利益。这正好说明,判决关于陈为李、蔡谋取利益的认定不能自圆其说。
可见,从客观行为上说,陈耀南是被动地接受他人为自己跑官,而不是变相收受财物并为他人谋利益。
(二)主观故意:是想收受财物、为他人谋利,还是想提拔重用?
受贿罪故意的内容具有双重性,即一是利用职务之便索取或者收受他人财物的故意,二是利用职务之便为他人谋取利益的故意,而且两个故意须同时具备,缺一不可。显然,陈耀南在争取“扶正”过程中既不想收受财物,也不想为他人谋取利益,相反却是为自己谋取利益,这似乎没有必要作过多的论证。受贿罪的罪过内容和其它故意犯罪内容一样,都具有认识与意志这两种因素。而陈耀南在此问题上都不具有这两个因素,在认识因素上,他是一不知已经花钱,只是最初听说要花钱,被他以“事未办成不能给钱”为由制止后,实际花钱的事情他并不清楚;二不知具体数额,他所看到的只是20万元人民币、 4万美金,因被他制止当时并没有花,后来的具体数额他并不清楚;三是不知该项费用的具体来源,缺乏受贿罪构成所特有的“对合对象”;四是不知该项费用的实际去向,不能认为为其“扶正”花费都未超出他故意的范围;五不知李贤志等人此时与他有什么“权钱交易”,因为双方根本就没有谈过为李等人谋取利益。在意志因素上,他丝毫没有接受李贤志等人财物并为他们谋取利益故意,愿意接受的是他们为其得到提拔重用而效劳。
一审判决认定陈耀南“故意的形式是一种概括故意,只要是为其“扶正”花费,都不超出其故意的范围”,这与事实不符。所谓概括故意是指行为人明知自己的行为必然导致构成要件的结果,但对结果的具体范围及其性质没有确定的认识,而希望、容忍或者放任这种结果发生的态度。概括故意是不确定故意的一种,是相对于确定故意而言的。在本案中,陈耀南对结果的具体范围是有确定的意思的,如对付款的条件是事情已经办成,付款的数额李贤志告诉他是几十万,他看到的也就是20万人民币、4万美元。所以,陈耀南的故意决不是概括故意,以“概括故意”的说法来论证陈耀南构成受贿罪在理论上是站不住脚的。
(三)贿赂标的:是财物,还是非财产性利益?
关于贿赂范围的理论争议自1979年《刑法》颁布以来就有不同认识。1997年修订《刑法》时,对于贿赂是否应当限于财物,曾经再次展开了热烈的讨论,但最终主张扩大贿赂范围的意见未被立法机关采纳。笔者认为,1979年《刑法》颁行以后,包括1988年1月21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关于惩治贪污罪贿赂罪的补充规定》,立法者的本意是把贿赂的范围只限于财物,司法实践中也是这样掌握的。修订刑法时,尽管有扩大贿赂范围的意见,而最终又没有采纳这种意见。按照罪刑法定原则,司法机关也只能把贿赂局限在财物上,才符合修订刑法的原意,而不能任意扩大贿赂的范围。
刑法第 385条规定,受贿罪的对象仅仅是“财物”,不包括财产性利益,更不包括非财产性利益。从实践来看,对接受他人提供的免费旅游、劳务等,并无认定为受贿的先例。这是符合现实国情的。目前,法学界普遍认为,“如果国家工作人员因为接受他人提供的“性服务”而利用职务为他人谋取利益,如果没有造成多大的社会危害性,则不管“性服务”的提供者为此花了多少钱,也没有必要一定要作犯罪处理,而是可以通过严厉的党政纪处分来处理。”与财物无关的非物质利益,如升学就业、招工指针、提升职务、迁移户口、提供女色等等,不能成为贿赂。
即使根据法院的认定,陈耀南只是粗略地知道李贤志等人为其得到重用而活动,至于李贤志等人为此的花费陈并不知情。在这里请允许笔者打一比方:某君好色,他的部下为讨好他,要为他花钱找外国女人,他表态搞成后才能付钱。结果他的部下被外国女人骗了一万元,某君也没有搞成。在这里某君愿意接受的是外国女人的“性服务”,而不是一万元。无论如何,哪怕某君搞成了,也不能认定其收受部下一万元财物。同理,在本案中最多只能认定陈耀南愿意接受的是得到重用的非财产性利益,而不能认定陈收受了李贤志等人的财物。也许是笔者孤陋寡闻,似乎闻所未闻这样的先例,有的倒是不以受贿论处案例:
2001年6月,广东省和平县补选县长,当时任县委副书记的钟洪茂,在人代会召开前,找人商议自己竞选县长一事。县委组织部副部长谢光明拿出1万元,给县交通局长叶耀东做贿选的活动经费。县人民医院副院长黄兰婕自己拿出960元买了6条毛毯,分送给 6名代表。钟的老乡、个体企业老板黄金水在选举前提供了4500元现金分给8名代表。钟“当选”为县长的当晚,黄兰婕请示钟洪茂后,又拿出4000元分给几名代表。2001年10月31日,只当了30天"县太爷"的原广东省和平县县长钟洪茂因破坏选举罪被广东省河源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判处有期徒刑 2年。后来,充当贿选“马前卒”的县委组织部副部长谢光明以贪污罪被和平县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3年。 似乎并没有看到,对钟洪茂以受贿罪、对谢光明、黄兰婕、黄金水以行贿罪判刑的报道。镇江市中级法院(2002)镇刑二初字第5号刑事判决所提及的、同样被侯万清、孙德文等人所骗的原河北省唐山市物资局局长闵有发,同意蔡国华为其联系提拔花钱19万元,也无以受贿罪被判刑的说法。
再如,被告人林某原系农行银行某中心营业部主任。他利用掌握审批贷款的职权,向贷户提出为其解决一套住房的要求,后者为以后贷款方便,以月租金400元一次支付48000元租下一套二室一厅的楼房供被告人居住,到案发时搬出,住了九个月。司法机关对于他取得住房是否能定受贿有分歧。一种意见认为,房租是可以用货币计算的物质性利益,被告人得到住房权,应认定为受贿罪;另一种意见认为,被告人得到住房权,没有实际得到财物,定受贿罪,法无明文规定,故不能认定为受贿罪。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人索取并居住贷户租赁的房屋,不认为是受贿。
(四)法院判决:是适用法律,还是变相类推?
应当承认的是,本案是一个一个疑难案件。它的难点有:一是卖“官帽”者是骗子,骗子又借“官帽”勒索钱财,向他“行贿”构不构成行贿罪?二是陈耀南参与为自己跑官的活动,但又没有经手跑官费用,又说了句“事情办不成不能给钱”,对他如何定性?于是,有人便想到将陈耀南、李贤志、蔡连银等人跑官的同向行为一分为二,形成对合犯罪,将直接被骗子骗走的钱在认定陈耀南处“中转”一下,变为李、蔡二人“变相”送给陈,陈再送给骗子。一审判决的理由即该款是“应由陈耀南本人出的钱”,实际上将买官费用合法化。这样,将陈的行为说成的“变相受贿”,从而“巧妙”地完成了两种不同性质的行为之间的转换,轻松地解决了这一疑难案件的法律适用。法院在适用法律时左右逢源,又能成功抵御各种来自外界的可能的质疑。这种“大而化之”处理办法,无疑是法官智能的结晶,闪耀着智能之光。但是,在罪刑法定的探照灯下,它却光芒尽失。
我国刑法中有对受贿如何惩处的规定,并没有“变相”受贿一说。如果将“变相”一词植入具体的罪名,则刑法所规定的所有罪名就会变成一只巨大的口袋,可以随意伸缩,将一切违法乱纪者尽收于法网之中。人们不禁要问,如果这能成立,那么不知什么时候又要出现“变相杀人”、“变相强奸”、“变相放火”?人们不禁再问,法院判决为何不使用具有确定性的法律概念而使用意义模糊的“变相”一词呢?人们不禁还要问,如果他人为一个人买官要定为受贿罪,那么他人为一个人买娼、买假护照、买毕业证,是不是也要按支付的数额定为受贿罪?在陈耀南案中,法院将陈默许部下为其“跑官”花钱的行为解释为刑法第 385条中的“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既不符合此种行为的性质,也不符合刑法第 385条的立法旨意,已经超越了合理解释的界限,而更具有类推适用的性质。法律的合理解释与司法类推之间仅一步之遥,但有着天壤之别;正如真理再向前一步,就可能是谬误的深渊!说一句既不中听又较为尖刻的话,认定陈耀南“变相”受贿,实际上是“变相”类推!
也许有人认为,认定陈耀南“变相”受贿,是解释而不是类推。但是,对刑法的解释不能背离罪刑法定原则的要求,更不能借法律解释之名,行类推适用之实。为了体现罪刑法定的原则,只有在解释结论有利于被告时,法院才能进行扩张或类推解释。而在陈耀南案中,法院恰恰作了不利于被告的解释。《南方周末》曾经刊登过一篇文章,标题是“不要冤枉坏人”,再简单不过的几个字,却是罪刑法定理念的体现。陈耀南不顾中央有关严禁“跑官”、“买官”禁令,确实不是无辜之人。我们不能误伤无辜,但是也不能滥伤“有辜”!一句话,对陈耀南的惩处,应当体现罪刑法定的原则。
以社会大众惯常的是非观念看,前述观点有可能遭到非议。“跑官”、“买官”毕竟危害了党和国家的声誉,具有一定的危害性。况且,在中央三令五申严禁“跑官”、“买官”的禁令之下,还发生这一丑闻,确实可恨。在这样的情况下,认为只有“从重”惩处才能证明党的纯洁性的想法,是可以理解的。然而,适用法律却不能带有这样的“情绪”,司法机关也绝不能以社会的政治评价和公众的道德评价来代替法律对行为的评价。适用法律一旦带上了“情绪”,就可能失去它的公正性,甚至变成令人恐怖的东西。
为了法律的公正性,人们呼唤:适用法律,不能带有情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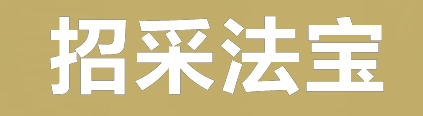

 2021-12-10
2021-12-10  浏览次数:次
浏览次数:次  返回列表
返回列表